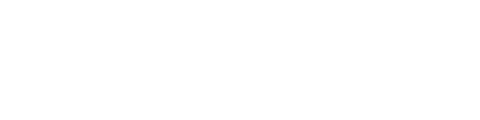中国80后养老危机逼近
有人说,80后生不逢时,是史上最悲催的一代。他们赶上了教育收费、就业难、高房价……如此辛苦工作了大半辈子,是时候退休享享清福了吧?对不起,即便二三十年后,他们的“九九八十一难”可能还没有结束。
近年来,我国人口生育率持续走低,已经引起了国民对“人口危机”的担忧,而这对于80后来说,意味着一场养老危机的逼近。
养老危机的逼近
不管你愿不愿意相信,我国步入老龄化社会已是不争的事实。
早在本世纪初,我国总人口中,65岁以上的老年人所占比重就已突破7%的基准线(联合国定义一个地区是否进入老龄化社会的标准)。而后的日子里,这一比重在持续攀升,从未出现过扭转迹象,2016年更是达到了10.8%(参见图1),也就是说,每100个中国人里,就有11个65岁以上的老人。

在此基础上,综合已有数据,我们可以将“65岁以上老年人占比从7%上升至14%所用年限”作为衡量老龄化速度快慢的标准。首先,来看一下其他国家的情况。
从IMF(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数据来看,英国、法国、美国、日本等发达国家均已提前步入老龄化社会,其中,英、法、美三国的老龄化速度较为缓慢,比如英国65岁以上老年人占比从7%上升至14%用了45年时间,而日本的老龄化速度则相对较快,仅用了25年便完成这一过程,而今,日本65岁以上老年人占比已经超过25%。
反观我国,仅仅16年的时间,65岁以上老人占比就从7%攀升至10.8%,倘若按照当前的态势发展下去,到2026年前后,我国65岁以上老年人占总人口的比重将会突破14%大关,前后加起来也不过25年左右,同日本的老龄化速度大体相当。
而此时此刻,日本举国上下正被老龄化困境所累,综合国力、社会结构、经济发展和人才培养等诸多方面都被人口老龄化严重制约。
老龄化趋势加重的另一面是年轻人口的锐减。查阅历年《中国统计年鉴》的数据可以发现,我国0~14岁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已经由2002年的22.4%下降至2016年的16.6%(参见图2)。同时,从人口普查数据来看,我国从80后到00后的不到一代人时间,出生人口萎缩了32%。

基于上述背景, “全面二孩”政策于2015年开始实施,旨在鼓励居民多生娃。然而2017年人口数据的低迷(出生人口与生育率分别为1723万人和12.43‰,两个指标双双下跌,其中出生人口更是远低于国家卫计委的预测数值)却让人们看到,居民的生育意愿并不强烈。如果低生育率态势一直持续下去,那么,随着时间的推移,未来我国的人口结构将发生质的变化。
根据联合国发布的《2050全球人口展望报告》,预计到2015年,我国人口年龄中位数为37岁(即一半的中国人年龄小于37岁,而另一半则大于37岁),到了2050年,我国人口年龄中位数将达到49.6岁,接近日本53.3岁的水平,而瑞典、英国、美国等欧美国家的人口中位数依然在40岁出头。值得注意的是,到2050年,36.5%的中国人都将在60岁以上,其中,就包括当前的80后群体。
如果真如《2050全球人口展望报告》所预测的那样,一场极其严峻的80后养老危机,或许已经伴随着历史的车轮步步逼近。
养老逻辑的漏洞
当前,我国实行的是统账结合的养老金制度,即社会统筹与个人账户相结合,一部分用于现在的养老,一部分积累起来用于以后的养老。具体来说,社会统筹部分的养老金为现收现付,由现在的年轻人交钱支付给现在的老年人养老;个人账户部分的养老金不断缴纳积累,用于年轻人退休以后的养老所需。
客观来说,这个养老制度既兼顾了社会公平,又照顾了缴费群体的利益。然而,现收现付的养老金越来越不够用了。根据2017年底人社部发布的《中国社会保险年度发展报告2016》,全国已经有13个省份养老保险基金累计结余的可支付月数不足1年,个别地区赤字超过200亿元。如此一来,唯有动用个人积累的部分来填补资金缺口。
据此,一个可预见的未来是:等到二三十年后,现在的年轻人退休了,却并没有攒下多少养老金,需要依靠未来的年轻人所缴纳的养老金来赡养。
然而,当这个“未来”到来之时,越来越少的年轻人与越来越多的老年人,前者是否能承担得起后者退休后生活所需的庞大开支?
也许有人会说,老人完全可以依靠自己的积蓄(如房产和投资)来养老,因而社会负担并没有想象中那么大。如果从宏观层面来看,这一观点是站不住脚的。
原因在于,不论是家庭养老、社会养老,还是以房养老、投资养老,本质上都是用工作人口创造的物品和服务来支撑退休老年人的日常生活,老年人口比例越高,社会整体养老压力越大,这一点毋庸置疑。
诚然,不少老年人是留有积蓄的,他们的积蓄来自于自己工作年龄时创造的价值,而这些价值所对应的商品和服务,在创造之后不久,一般都已经消耗掉了。所以,养老积蓄并不是老年人把当年创造的商品或服务储存下来供以后使用,而是变换成为存款、证券或房产等投资凭证,等到养老需要时,才用这些凭证来兑现后面工作人口所提供的商品和服务。因此,养老积蓄作为名义财富,在兑现时的价值取决于这些积蓄所对应的未来财富的价值。
然而,按照目前的态势,未来我国人口衰减这一剧情很可能会上演,届时,经济增长也便不再强劲,人们创造的价值也将会随之萎缩,这样一来,养老积蓄所代表的名义财富的“账面性”也就越强。此外,某种程度上讲,老年人手里占有的名义财富越多,他们的兑现能力就越强,这便意味着工作中的年轻人在自己创造的价值中能留给自己享用的财富份额就越少,压力反而更大。
2017年3月份,人社部领导在《“十三五”国家老龄事业发展和养老体系建设规划》新闻发布会上说过一番话:
“截至2016年底,我国60岁以上人口已达2.3亿人,占总人口的16.7%,65岁以上人口达1.5亿人,占10.8%,据预测,我国老年抚养比将由目前的2.8:1达到2050年的1.3:1。”
翻译过来就是:我国现在是2.8个人赡养1个老年人,而到了2050年,很可能会演变为1.3个人赡养1个老年人——而2050年的老年人,正是今天的你我。
现实状况的残酷
当然,放眼全球,养老危机并不是新鲜事物,世界上有不少国家已经或即将面临着这一难题。在此,以正在经历养老危机的日本和希腊举例:
日本:根据日本厚生劳动省统计,2014年普通日本中产家庭,夫妇两人每月一共领取的养老金为21.8万~23万日元。然而,东京中等偏上的养老院,入住者每人一个月要支付20万~40万日元的费用,入住时还要一次性缴纳入住金,正常是月额的3~6倍左右。即便是条件偏下的养老院,每个月费用也要在13万日元左右。显然,养老金在老人日常开销方面能起到的作用非常有限。于是,大多数职工退休后还是选择了再就业的方式来赚取生活费用。近年来,日本街头的出租司机、工地看护、交通保安、高速收费员、物业管理员、清洁员等职业的阵容里,出现了越来越多的老年人。
希腊:希腊之所以会经历债务危机,其根源之一就是希腊严重的老龄化程度。2010年,希腊的公共养老金支出占GDP的比重为11.6%,2015年更是花了22.7%的普通财政预算来填补养老金漏洞。受制于老龄化保障的财政支出快速飙升与劳动人口规模的萎缩,国民经济的生产力、消费力、发展力不断下降,收入无法覆盖支出,最终只能继续通过政府举债弥补缺口,并最终导致政府债务危机。
相比之下,我们需要思考怎样应对正步步逼近的养老危机。至少,下述两点需引起重视:
第一,“未富先老”或将加剧养老危机。虽然日本是全球老龄化最为严重的国家,但是其国民富裕程度远胜于我们。从数据上看,日本的人均GDP始终遥遥领先我国,即便近年来经济形势动荡不安,但在2016年,日本的人均GDP依然是我国的近5倍(参见图3)。可以说,日本是富裕的老龄化社会,而我国未来的老龄化状态,则会呈现出“未富先老”的情景,贫困的老龄化势必将导致人均财富与养老需求之间的缺口更大。

第二,房价高企让养老成“伪命题”。“4-2-1”(四位老人对应夫妻二人和一个孩子)结构,已经成为当下我国老龄化社会的形象写照,似乎看上去年轻人的隐形负担会越来越重。可事实上,大量年轻人却正在“啃老”。从全社会的宏观层面看,年轻人创造的财富用于赡养老人不假,但从家庭层面看,却是老年人拿出一生的积蓄和退休金给子女买房。换句话说,我国养老成本逐渐加重的同时,老年人也在供养年轻人,甚至年轻人的下一代。中国青年报社会调查中心报告显示,97%的受访一线城市年轻人表示身边人买房要靠父母。由此可见,受高房价的影响,捆绑父母买房已经成为年轻人的常态。而此时,养老可能已经是个伪命题,情况可能比我们想象得要严峻,或许真的是时候去做些什么了。
我所憧憬的未来
未雨绸缪,总是好的,千万别等到掉进坑的那一刻才有所觉悟。
如何针对未来养老危机这一人类共同难题,世界经济论坛的研究报告给出了几点建议,包括延迟职工退休年龄、奖励在职期间储蓄、调整养老金制度等。而这些都是涉及民生的重大举措,如何参考这些建议,并根据我国具体国情来制定切实有效的政策,也着实是对国人智慧的一次重大考验。
此外,我们还应当反思,如何通过完善公共服务体系以及灵活运用多种政策手段来鼓励生育,同时着手创造福利条件来缓解年轻人对生育的“胆怯”。
毕竟,今天的年轻人在未来退休后,如果能够有足够规模的下一代年轻人作为他们的养老保障,那么危机便会缓解很多。
临近尾声,我们不妨畅想一下未来:
等到今天的10后们长大成人,他们会发现自己是独生子女,他们的父母80后也是独生子女,“4-2-1”的家庭结构虽然没有改变,但好在他们无需再为房价而担忧,因为人口规模的萎缩会导致大量空置的房产被释放出来,房价会下跌,生活成本也不再高昂。届时,他们或许不用像今天的我们一样,整日为“中产危机”所困,被债务所累,而是可以轻装上阵地去投身于技术与制度变革,进而催生国民经济新的增长点,并引发新一轮“婴儿潮”……
事情究竟会如何发展,身为80后的我无比期待,尽管到时候,我们已近古稀之年,行将就木,与世无争。
(来源:苏宁财富资讯;作者:苏宁金融研究院研究员付一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