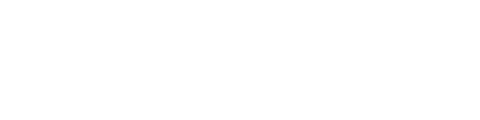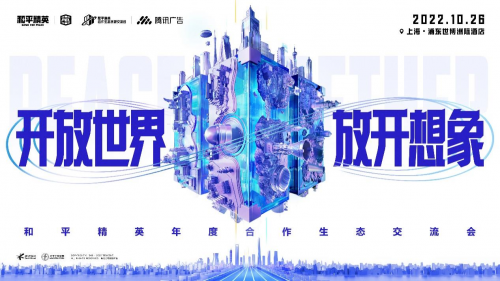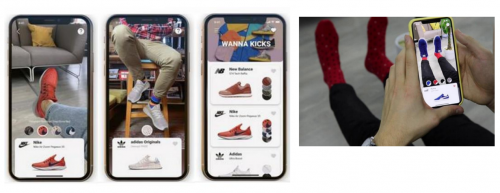疫情的反复不断给创业者们施加不确定因素,无论是时间还是经济成本,都在一项一项叠加。即便不是严重依赖线下客流获得收入的服务型业务,也遇到了办公场地、政策限制的影响
寒气之下,年轻的创业者都受到了不小的影响,但是无论创业失败还是保守推进,都可以在这些年轻人身上找到乐观的精神

图/视觉中国
文 | 实习生 刘嘉欣 王莘莘
编辑 | 余乐
郝一鸣手头的“数字克隆人”项目刚刚开始有些进展,前不久他从杭州去了趟北京,经别人介绍接触到了芯片巨头英伟达,在那里做了一场路演。“也不是立马就要找到投资,但是需要去社交一下。”
近一年来,郝一鸣一直在为自己的项目找投资人,但是结果并不如意。之前聊过的投资人都说项目不错,但到投钱的时候就都开始观望。他能明显感觉出来投资人变得越来越谨慎和保守。
“现在他们更希望做那种锦上添花的事,看到这个项目可以赚钱了再投,在此之前都会说:‘你先做做,我们再聊。’”
郝一鸣2020年毕业于四川传媒学院, 2019年开始筹划创业,毕业后不久就付诸实施。目前他已经为此投进了十几万元,除了自己的存款,还有父母的支持。像他这样刚毕业就创业的大学生,如今已经不多了。他不止一次地说:“脑子不正常的才创业”。
大气候降温
几年前,大学生创业是一件很时髦的事情。2015年,国务院正式出台《关于大力推进大众创业万众创新若干政策措施的意见》,各省市响应国家政策纷纷涌现出创业孵化基地,象牙塔里大学生创业的热情也水涨船高。彼时,高校在校园里会专门设立创业基地、创客空间,学生只需提交一份像样的计划书,就可以拥有一间办公室,还能享受学校的政策性补贴。
如今,受到严峻就业形势和后疫情时代的种种影响,创业的大环境没有以前那么友好了。
郝一鸣的项目是做基因数据生成虚拟形象,因为涉及基因,在大众的认知里还担忧有隐私泄露的风险。教育市场是一个长久的工作,但当下更重要的问题是,投资人手里的钱也不多了,投资倾向保守,初创阶段的项目在投资人看来风险极高。
同样感受到环境在降温的是在成都读书的杨喜堤。他在2020年的时候拿到了普渡大学的留学机会,正好赶上新冠的第一年,出国读书变得遥遥无期。他本科专业是动物科学,计划做自己“猪芯片”的业务。所谓“猪芯片”其实指的是一种猪遗传育种系统解决方案。
现在,杨喜堤一边读博士一边创业。他把之前和朋友创立的软件公司转向研究算法和技术,还和两家工程建筑企业合资在云南筹备建猪场,估算总投资1.2个亿。建厂是重资本投资,杨喜堤最开始就没往找投资人这方面想,觉得成功的概率比较小,建厂资金的筹措还是靠合资的建筑企业出资,以及走传统的银行贷款渠道。
杨喜堤告诉我们,云南建场的资金和成都的公司团队目前运转良好,不过疫情确实拖慢了猪场的建设进度。主要原因在于合资方是工程企业,依赖上游房产企业的订单。房地产行业不景气,企业手头的资金紧张,只能放慢建场的进度。猪场由原本一次建成改为分期建设。
像郝一鸣和杨喜堤这样的创业者,感受到的大多是投资方和上游产业传递下来的寒气。而对一些依赖线下的实体创业者来说,让他们不得不停下脚步寻求其他出路的,还是因为疫情。
1999年出生的范范,2022年才刚刚本科毕业,但他的创业之路从大三时就开始了。当时,范范正在一家摄影馆里兼职做摄影师,萌生了想开工作室的想法。因为了解现成的商业模板,他和一位同事一拍即合,打算合伙开店。第一笔启动资金需要四十多万,范范硬着头皮跟家里借了钱,加上自己兼职攒下来的积蓄,一共十万,占店里20%的股份。10月份,工作室就正式开始营业了。
营业初期为了获客,范范和合伙人刻意压低每单的价格,开店不久就在美团的休闲娱乐板块上做到了南京的前三。不过,当时的客单量是靠着前期大量低价单撑起的,离盈利还差一截。正当范范憧憬着生意能够逐渐走上正轨的时候,3月底南京的疫情给他来了个措手不及。客人无法到店消费,平台上预付的钱也就到不了范范手中,而此时刚好到了季付房租的时候。十几万的房租,几个合伙人都没钱再垫进去。
合伙人立马决定及时止损,但范范还是希望能再支撑一个月,看看疫情会不会好转。商量过后,他们用了押金抵作了最后一个月房租。等到4月,情况依旧没有好转,他们只好变卖店内物品,关闭店铺。范范投进去的钱,亏了一半还多。
像范范这样的不在少数,疫情的反复不断给创业者们施加不确定因素,无论是时间还是经济成本,都在一项一项叠加。即便不是严重依赖线下客流获得收入的服务型业务,也遇到了办公场地、政策限制的影响,在山西的郭鑫享受学校创业基地的便利,一直在学校里办公。自从疫情以来,学校进出政策更加严格,而郭鑫和团队也毕业了。他们只好从学校搬离,在市中心高价租了写字楼里的一间办公室。
杨喜堤还提到,今年来找他聊创业的人明显变少了。“以前会有很多人来问我的意见,让我帮他们看看商业模式是不是可行,很多的商业模式我其实都感觉没必要做,但是大家都很热衷搞这个。”但是现在,所有企业都变的很谨慎,不愿意朝外面投资 “所以我一直说,现在不是创业的最好时候。”
务实,不再好高骛远
年轻人普遍选择求稳,敢于创业的越来越少。不过,现在选择创业的毕业生已经很少有那种头脑发热、盲目跟风的人了,他们大多都是上学时就开始了创业准备,有一部分在校期间就积累了足够多的创业经验和资源。
大学生们的创业选择也更加务实,不再像前几年那样盲目追逐风口,而是更多地从自己的所学专业和特长出发,选择能够尽快产生正向现金流的项目,哪怕项目本身听起来没那么“高级”。
2019年的夏天,涂陈昊还在紧张地准备考研。紧张而投入的复习让他很痛苦不堪。“或许不太适合考研这条路呢?”他悄悄在心里打了退堂鼓。复习进行到了10月,最终决定不考了,一位老师和他说可以试着创业。
在校的前三年涂陈昊经常会接一些影视相关的活儿来赚零花钱,这些资源大都是老师、同学介绍的。这次也不例外,建议他创业的老师,介绍了一些项目资源,涂陈昊的创业就此开始了。
2020年12月,公司正式建立起来。注册的流程并不麻烦,5000元注册公司,做虚拟地址的费用,2400元每年的代记账,“当时一口气交了7400块,营业执照第二天就下来了”。公司成立的时候,团队的主力其实也就只有三个合伙人。
涂陈昊至今记得第一单业务接的是中国农业大学2019年就业质量报告。“当时我们是先给传媒大学做了一个就业质量报告,后来老师说你们这个做的挺好,农大看到了也想做,就问这个是谁做的,老师就把我们介绍给他们了。”报告前前后后忙了三四个礼拜,进账了第一笔钱2万元,“这是我们公司的第一桶金,开的第一张发票就是这单的。”因为第一次开发票,涂陈浩搞的手忙脚乱,先是把票放反了,然后又打印出界了……光开那一张就废了六七张发票。
在创业初期,因为中国传媒大学在媒体业界的背书和老师介绍资源的加持,涂陈昊走的非常顺利。和疫情中屡屡受挫的创业者不同,公司甚至在疫情的时候迎来了小风口。2020年春天,涂陈昊从老家回到北京,发现当时虽然疫情导致很多企业停工,但是媒体和公司还是会有宣传的任务和要求,但是找不到执行的公司。经过人打听,这些公司最后找到了涂陈昊,“可能当时北京的一些团队也没回来,总之就是没人接活儿。”2月到5月这段时间,涂陈昊接了3、4个项目,给团队带来了一笔不小的收入。
涂陈昊承认自己是幸运的,因为创业到现在一直比较顺利,父母也从最初的不太认同,到“能养活自己就行”的支持态度。
与涂陈昊类似,很多学生的创业路都是从学校的创业扶持项目里开始的。申报项目、参加创业比赛、项目落地。
来自福建省的李琰婕现在经营了自己的袋泡茶品牌“茶享时”,这个品牌的诞生正是从本科时期参加的“大创”项目(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计划)发展来的。李琰婕的本科学校和专业都和茶有关。在导师的指导下,她尝试了很多茶叶深加工的产品,因为技术壁垒,大部分都还停留在实验室阶段。于是,李琰婕就和团队成员们就决定从袋泡茶入手,最终获得了大创的省级立项。
从0到1的大学生创业故事,也成为了她们在小红书上品牌宣传的主要卖点。
另一位创业者威利的第一桶金,也来源于最初在学校的“小打小闹”。威利本科在一所体育类大学,想要改善生活赚零花钱,他就开始做起了校园文化衫代理。2019年6月,他组建了一个公众号团队,以学校内的学生为资源,谈下来许多代理业务,包括资格证培训、鲜奶配送、羽绒服售卖等。2020年开始,公众号有所起色,他们也开始接到微信公众号广告投放,单条价格在500元-800元。
他们的项目获得学校的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立项,搬进了学校提供的“创客空间”,有了自己办公的一小片区域,也拿到了学校官方的一些称号。增加影响力的同时,也让招募新成员更加简单了。他还参加了挑战杯等一系列比赛,不过因为团队并没有一个主导性的产品,参赛项目并未走出学校,各种比赛奖金不到一万。
这个年龄,经得起失败
在校园尝到了创业的甜头之后,威利打算“走出”校园闯荡, “既然在学校内都有各种合作自己找上门,那去外面肯定有几何倍数的增长。”
但是真正办好休学手续,搬出来之后,威利并没有接到更多的合作邀约,疫情也仍然反复。他坦言,“入局前看到的都是机会和收益,做了之后才认识到风险和成本。”今年回到校园读大四,面对就业的抉择,威利选择了考研,跨考国际商务专业。
他认为,局限于学生身份,本来就不太可能做大。“之前不能称得上成功,当然现在也不算是失败。”对于他来说,这段创业就像是一次现实的经营游戏,获得更多的是体验,赚到的钱是在体验之余而获得的经济回报。
经过了做代理、办公司、做自媒体的这些尝试之后,威利反而认识到现在的时机还不太充足,人力、团队、项目都不成熟,现在做成功概率很低。他保守地选择报考一所北京的综合类高校,今年唯一的目标就是考研上岸。
开摄影馆的范范半年创业之路也告一段落,但他从未怀疑过自己当初创业的决定。范范直言,“我更看重的是这段经历中的成长,无论是在心态上还是为人处世上。如果能够量化,我的成长绝对比亏损的金钱要多。”毕业找工作的过程中,这段创业经历也对他有不少帮助,面试中HR会着重问他这段经历,最终成功拿到了offer。现在工作之余,范范也开始经营起了自己的小红书账号,希望未来能够发展成一个副业。
“我现在这个年纪完全亏得起,又不是亏了上百万。”他现在还欠着家里3万元。关店之后忙着做毕业论文、处理毕业事宜,9月份才找到了工作,薪资待遇他很满意。从3月份大概知道店铺做不下去后,范范就有了心理准备。对于这个结果,他能坦然接受。
“创业失败”这件事在创业者们看来,并非是对于人生的全盘否定,更多获得的反而是经验和成长。范范和威利都认为,创业失败让他们认识到了自己暂时还不适合做这件事,无论从能力上还是阅历上。
这种心态也和这批学生创业者的创业处境和创业观念相关。郝一鸣说:“我没有负债,没有卖车卖房贷款,就算这件事情搞不成,对我也没什么损失。”年轻意味着没有家庭和其他支出,“一人吃饱全家不饿”。如果工作几年之后再创业,家庭、中年危机的压力会一个一个找上门,这个时候如果创业失败,就会有负罪感。
郝一鸣还观察到,自己接触的数位投资圈的人,很多都像长辈一样对他,“大家会觉得你是小孩子,很多事情都愿意教你带你,但如果等到年纪大了,一旦什么做不好,别人就会觉得是你不会做事。”
大环境的变化在杨喜堤看来,只是意味着解决问题的难度提升了,并非不可解决。似乎创业者身上都有一种纯真的乐观,“我一直坚信只要事情本身能创造价值,项目肯定有生存空间,肯定能做下去。只是说,项目能不能按照你一开始最理想的方向和方式去发展,这个是需要调整的。”
不可否认的是,创业者们不论再怎么乐观,他们也开始更加谨慎,主动或者被动地放慢脚步。
李琰婕此前做的高校公众号和跨境电商项目都是因为受到疫情影响而被迫中止的,因此,在拿到投资做茶品牌的时候,她变得更加谨慎。创业的过程中,李琰婕考上了广西大学农学院的研究生,还拿到了她老家的事业编工作。与合伙人商量过后,她踏上了去广西大学读研的路途。现在的她一边进行研究生课程更系统专业的研究茶叶,另一边还负责品牌的运营和新品开发。
郝一鸣还在杭州坚持着,他告诉我们,等进行不下去、卡住了,他打算再回成都继续打工,攒一些钱再继续回到杭州的公司。现在看来他的项目还在有序地进行中,已经有了一批用户。就等有投资人可以投给他们一笔资金,来支持项目的完全落地。和所有创业者一样,一鸣一直认为自己的“数字克隆人”是一个有价值有市场的东西,既然有空间有需求,一定能行。
杨喜堤还在积极的和各方谈接触,接受采访前刚和北京超算中心打电话谈合作。整体上来看,杨喜堤的公司和项目依然在平稳运行,猪场建设只是整个项目环节中的一个小问题。
涂陈昊前几天在朋友圈发了团队招聘的信息,文案是“好消息是,新来的朋友们可以直接入驻新场地,与我们一起共创未来”。